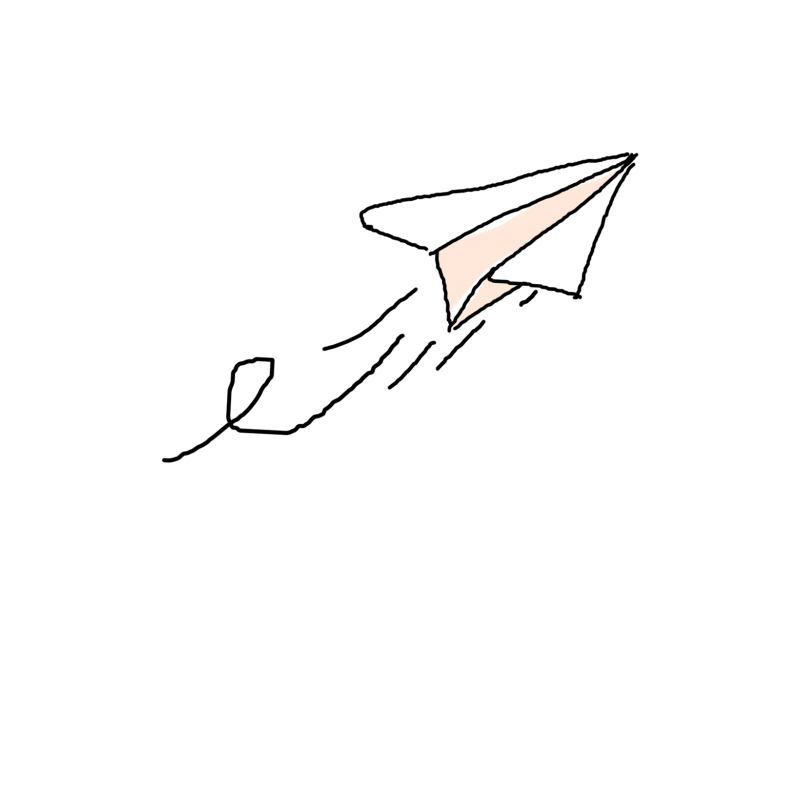自信爱读书,看了纳博科夫,自卑不已。与之相比,我那只能算吞书,尚未入门,难怪消化不良。
自信懂人性,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,目瞪口呆。我分析起人性,也说得头头是道;剖析起自我,也够冷血无情。但与之比起来,不过是九牛一毛。人性中还有什么没有被他道出?我得赶紧找找。
自信爱艺术,看了木心,心都凉了。我连何为艺术都不晓得呢!竟奢谈爱艺术。
纳博科夫教我读书, 我说我正在读《包法利夫人》,他问第几遍,我答第一遍,他立马暴跳如雷,第一百遍时才能叫读。可不敢说我还在读《罪与罚》。这个后半生都住在酒店里的俄罗斯汉子丝毫不念民族感情,将陀思妥耶夫斯基骂得狗血淋头,将其作品贬得一文不值。
陀思妥耶夫斯基教我心理学,我惶恐不安,生怕哪一天他突然跪在我面前向我忏悔。
木心给我补课, 我问何为艺术,他答读福楼拜读尼采读陀思妥耶夫斯基。
木心爱写俳句,爱说俏皮话,我附庸风雅,每日也来几句,俳句不够俳句,格言不够格言,俏皮也不够俏皮,姑妄写之,算作碎语闲言。
萨特说,他人即地狱。我眼睛一亮,牢记心间。如今看来,他人有时也是鞭子。
在路上走着,一回头,咦!人呢?
我所追求的,正是他人唯恐避之不及的。
在一架独木桥上来来回回,终于掉了下去。
起初,读书囫囵吞枣,写作一气呵成,为人吊儿郎当,说话颠三倒四。此为瓶颈。我有句:木心,你劫我见艺术,我知道错了。艺术是霍小玉,我是李益(这是个不要脸的比喻),木心是黄衫客。
我时而狂妄时而自卑,狂妄是因为无知,自卑是因为知道自己无知。
我连怀疑都怀疑。
除了折腾自个儿,我别无所长。
据说,福楼拜说过,包法利夫人就是我。我有句:精神上的包法利夫人一死,福楼拜方才成其为福楼拜。
叔本华有名言:像伟人一样思考,像普通人一样说话。这是教有思想的人应对世俗,或者说教他们谦虚做人。我有句:像上帝一样思考,像魔鬼一样说话。此乃时代嬗变之后果。然后呢?理论就是不实践的意思。
我想把梦写下来,这也是梦。
蒙田论读书,分明就是陶渊明之不求甚解,高则高矣,却如饱读古书的鲁迅让国人莫读古书,我尚有自知之明,赶紧逃到纳博科夫的课堂去挨骂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,辞官归隐,蒙田不得已当了市长。我有句:蒙田,法国的大半个陶渊明。
阳台对面有一排不知名的树,枝繁叶茂,郁郁葱葱,雨洗后更是叠青泻翠,绿得晃眼,搜肠刮肚,不能形容。恰读钱锺书之通感论。惊其美,喜其妙。此句油然而起:微风抚枝头,绿叶烧人眼。
钱锺书三个字能让人想到什么?照相机记忆、学问渊博、语言天才、书蠹、文化昆仑。人的劣根性包括只艳羡他人光鲜靓丽的衣服。我有句:所谓天才,不过是有组织有预谋地坚持兴趣的一小撮人。
老子说,天地不仁,以万物为刍狗。这是偏见。天地何曾不仁又何曾仁过,天地非仁也。然而,偏见是对庸见的忍无可忍。
纳博科夫说了,风格和结构是一本小说的精华,伟大的思想不过是一句空洞的废话。这分明是一个伟大的偏见。
我有一个不太高明的句子:概括中心思想是对艺术的强奸。
读书之间的不读书是一种反刍,深思之间的无思亦是。
读博尔赫斯,到结尾,又被骗了。木心说,读个三四遍再去卖弄吧!
关于引用,畴昔因噎废食,觉得引用是一种偷懒,甚至是一种卖弄。李宗吾读书有三步:以古人为敌,以古人为友,以古人为徒。人之思想皆来自大脑,人之大脑皆有无意识,荣格称之为集体无意识,此乃人思想之根本。所以,所罗门才说太阳底下无新事,柏拉图说一切知识都是回忆。别人说了自己想说的话,完全不必大惊小怪,刻意不引用也全无必要。别人说的没我好,以之为敌,弃之不用;别人说的比我好,以之为友,引用之。
古人不是说,先我注六经,后六经注我。
宇宙观:混沌→有序→混乱
人性观:禽兽→人→禽兽不如
生死观:生不过是死前的一段景象。
自我观:我不过是一个去了势瞎了眼不嬉皮的嬉皮士。
极端地厌恶极端。
唯一一句像俳句的俳句:我思嵇康贤,深林长啸青白眼,风骨不复见。
虚无作如是观。